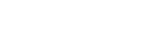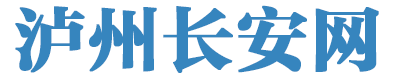□ 魏言
破晓,山村一片寂静。“快点起来,趁清早凉快,抓紧干活路。”记忆中的暑假,母亲总是每天准时唤醒睡梦中的我们。
在她不停地催促下,我们睁开惺忪的眼睛,哈欠连天,磨磨唧唧地溜下床。“老大、老二、我和你爸给红苕薅草。大女扯猪草、煮饭。老幺唛,你照旧。”母亲像指挥官一样给全家人铺排着各种任务。
老幺是我,那时候刚读小学四年级,姐姐待字闺中,大哥二哥分别读高中初中。母亲嘴里说的“照旧”,指的就是给家里那头大水牛割草。三十年前的农村,家家户户都在喂养牛,多则两三头,少则一头。我们家这头大水牛在全村几百头牛中体型最彪悍,力气最大,常常被借去耕田犁地,是全村人眼中的宝贝疙瘩,也在家里享受着特殊的“待遇”。我给它取了个名字,叫“大黑”。
夏天的农村到处蔓藤缠绕,草类繁多,但更常见的是狗尾巴、铁萱草等杂草,牛最爱吃的皇竹草却很少。皇竹草长在水塘边和比较潮湿的山林里,高高壮壮的根茎上面长着很长很宽的叶子,叶子的边沿密密麻麻地长着小刺。这种草叶厚,水分多,味微甜,还有清热解毒的功效。
我年幼且个头矮小,母亲总是给我安排给大黑割草这件轻松活儿,让大哥二哥羡慕不已。“硬是皇帝爱长子,百姓爱幺儿嗦!”大哥二哥一边嘀咕着,一边慢腾腾地扛起锄头,跟着父亲母亲出了门。他们前脚刚走,我又睡起了回笼觉。
“老幺,赶紧起来,大黑快饿死了!”姐姐摇醒了正在做梦的我,而此时太阳已上三竿,扯完猪草的姐姐早已回到家煮饭了,灶屋里飘来阵阵饭香。
我“嗖”地一下跳下床,拿起锋利的镰刀,背上家里最大的背篼,像利箭般冲向二里外的堰渠。这个地方我昨天侦察过,生长着一大片皇竹草,足足够大黑吃上两天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飞奔到堰渠旁,丰美茂密的皇竹草已经不见踪影,眼前只剩下一片拳头高的草桩,在阳光的照射下,草桩上淡白色草浆直刺双眼。
“完了,这下完了!”我瘫坐在地上。泪眼朦胧中,我仿佛看见家里几百斤重的大黑停止了叫唤,瘪着肚皮躺在牛圈里,双眼紧闭,长长的尾巴一动不动……
突然,身后有人拍我的肩膀,回头一看,是姐姐。我像看到救星一样,紧紧攥着她的手问:“姐,咋办啊?大黑真的要饿死了。”
“哎呀,老幺,我也帮不了你……”姐姐的瓜子脸上挂满了愁云。我脑袋“嗡嗡”直响,只感觉天旋地转。稍许,姐姐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头,“有什么事我顶着,全家都在等着你吃饭呐,走,回家!”
白花花的太阳高悬中天,灼灼热浪迎面扑来。狭窄的田坎上,姐姐帮我背着空空的背篼,我紧跟在她身后,脑袋犹如路边稻田里的穗子一样耷拉着。快到家了,我静静竖起耳朵,多么希望大黑像往日那样“嗷嗷”叫着。但却听到的是母亲在牛圈里大声喊道:“大黑,起来,起来!”
难道大黑真的饿死了?我的脑子一片空白,呆若木鸡地站在院坝前,脸蛋上挂着两行眼泪。“老幺,真的没事,擦干眼泪,进屋!”姐姐齐齐的刘海下面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转动着,嘴角露出浅浅的微笑。在姐姐连拉带拽下,我来到了牛圈栅栏前,定眼一看,满头大汗地母亲正一手提着装满水的木桶,一手拿着高粱刷子在大黑身上刷来刷去,油光水滑的大黑眯着眼睛,鼓着大肚子惬意地躺在地上,嘴里“哐哧哐哧”嚼着新鲜的皇竹草。
几缕阳光从牛圈房顶的缝隙中投射进来,墙角处一大堆嫩生生的皇竹草泛着绿油油的青光。母亲乐呵呵地说:“老幺,你姐告诉我,你割了这么多草,能干!”
我恍然大悟,原来是姐姐帮我割回了皇竹草,我转过身,而她却没了踪影。此时,灶屋里传出了她那百灵鸟般的声音:
“开饭咯——”
(作者单位:四川省公安厅)